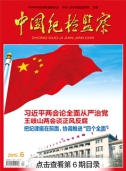

社论
要闻
两会专题
时评
论坛
执纪
监督
风范
警示
环球
新风
文苑

社论
要闻
两会专题
时评
论坛
执纪
监督
风范
警示
环球
新风
文苑
分析意见
我们认为,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应统一认定为受贿性质,其自行用于公益支出的5万元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
首先,应从职务性质是否具有公务性以及任职是否具有连续性两个方面判断张某行为性质。
我们认为,本案中张某于工行改制后的履职行为应认定为实质上的委派。理由在于,虽然工行改制后没有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主体对张某重新履行相关委派手续,但张某在改制后的企业中仍然担任原职,其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并未改变,亦无其他新的任命阻断原职权来源,其在改制后的工行中仍然实际承担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保值、增值职责(当然,不可否认亦同时负有对非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职责)。
如果基于实践中工作的不规范而不将继续担任改制后企业相应层级的管理人员认定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必然造成改制企业中无人代表国有资产履行职责的局面。执纪、执法实践中办理该类案件时,既不能不看行为人的身份,也不能太拘泥于行为人身份。对于实践中确无书面或相关证据证实存在委派程序,但亦未经改制企业选举,行为人事实上还是履行改制前单位原有职责的,关键从两方面对行为人身份进行实质判断和综合认定,即职务的性质是否具有公务性,以及其任职是否具有连续性。
就本案而言,张某原系国有单位从事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人员,虽然其在改制后的单位任职没有国有单位形式上的委派,但在该国有单位改制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后,张某仍担任原职务,继续从事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其职务的性质仍然具有公务性,同时其任职保持连续性,故张某在工行改制前后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利用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具备受贿行为的特征。
其次,“为公而用”的受贿财物原则上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但亦有例外情形。
用于公务、公益的受贿款项能否从受贿数额中扣除,理论界及实务界主要有“扣除说”、“不予扣除说”及“区别说”三种观点。我们认为,贿款的去向是否影响对受贿性质的认定,必须从受贿的本质特征及受贿的基本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受贿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危害性亦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而无关收受款物后如何处置,即受贿人在受贿完成后将贿款用于捐赠等公益或其他公务支出并不会减损先前受贿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只要行为人出于受贿故意并收受他人财物,受贿全部构成要件完备,应认定为受贿性质。至于收受贿赂后是将款物占为己有还是给予他人,是归个人使用还是归他人使用,抑或用于公用或公益支出,均应视为完成受贿行为后对赃款的处置,不应影响受贿性质的认定,自然也不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但考虑到赃款的使用若具有积极意义,与单纯满足自身欲望、完全占为己有存在些许差别,在不影响定性的前提下,可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定量情节予以考虑。
当然,实践中应在坚持上述认定原则的基础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并非出于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单位利益主动收受他人财物,收受以后及时上交用于公用或者无法及时退还而确用于公用的,鉴于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一开始即无个人受贿故意,故除符合单位受贿性质的,一般不应作为个人受贿认定。对于行为人被动收受他人财物后(即无奈收受型),及时将款项用于公用或者上交单位账户,并向有关部门说明款项来源的,鉴于行为人及时上交及主动说明情况的事实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并无受贿故意,故所收受的款项亦不应认定为受贿对象。
本案中,王某虽然将收受款物中的5万元用于公益支出,但鉴于其并未公开该款项的来源和性质,款物仍处于行为人个人实际控制之下,其用于公益支出系个人行为,且无证据证实其先前收受他人财物系为单位利益或因客观原因未及时退还而用于捐赠,其收受他人财物的先行为已构成受贿,故其公益支出5万元这一后行为自然属于受贿完成后的赃款处置性质,不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但不影响其视情况作为酌情从轻处理情节予以考虑。